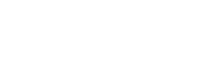星空体育app取款:
江淮丘陵的大地貌,这是若干年后,我坐飞机经过桐城的上空时看见的。再后来,在各种画册和视频中,那片土地以起伏绵延、山水相依而不断地让我心动。但是,在我的幼年、少年即人生的最初岁月里,我一直住在那个叫洪庄的小村庄里。我无法感知到大地整个的地貌,只明白我们的村庄坐落在从北向南的缓坡地带。北边,是一条巨大的岗脊,后来,成为一个水利工作者后,我知道那严格的学名叫分水岭。水以脊分,向东南或西北流淌。而最终,这些水都汇合到了著名的菜子湖、嬉子湖中,并经由这些湖泊,流入浩荡的长江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那也是一块滨江之地。每年春节,从彭泽、从南京、从九江回来的大姑、三姑和小姑,遇见人总被打招呼道:“从江南回来了?”啊,她们那边叫江南,那么,我们这边就叫江北。

从栀子河岸上看我们村庄,狭长形的,卧着,如同一只蚕。如果目光越过村庄,就会看见那棵给我植物启蒙的树——青桐树。
这是一种村庄上不多见的树。有一段时间,我曾不断地想:它为啥不多见?后来,我想明白了。原因在它对土壤的选择,在它对阳光的选择,在它对风的选择。更在它对独立的个性的选择。
村里的老先生对我们解释树木时,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“众木成林”。树跟人一样,是群居性的。即使一树荒瘦的小老松,它也会挤在一堆小老松之间,构成了山岗上那片倔强的小松林。但是,青桐偏不是。青桐唯独一棵,立在离村庄两里地的高埂上。高埂上还有高埂。高埂下是一大片农田。站在栀子河岸上看到的青桐树,远远的,像一杆旗帜,青色的,孤独而坚韧地立着。
青桐的四周,都是些低矮的植物。野蔷薇,攀根草,蛇莓子,狗尾巴草,以及四季都开的小野菊……青桐不管不顾地独自站立着。我站在树边,看了很久。这甚至是一棵没有鸟儿来光临的树,是一棵没有同伙来鼓励的树,是一棵没有更多的花草陪伴的树。
回到村子里,大人们告诉我:它叫青桐。青桐的树皮能做棕绳,树叶能用来晒酱。树木结实,但成材的时间太长。因此,在乡下,它只能是一种被冷漠的树。很少有人特意种植。往往是它的种子飞到了哪里,然后便悄然长出。再后来,长高了,长大了,便被用来制绳,晒酱。大人们说:“别小看了它。它最抗风,最选土,性子最犟。”
为了这记住,我时常会在栀子河远远地望这棵青桐树。或者跑到村子东头,不远不近地望它。终于,在夏日的暴风雨中,我看见它迎风摇摆着,像个跳舞的人,树枝被刮折的幅度,差一点就成了直角。风从不同的方向打击它,整个雨幕中,它就如同一位战士,不声不响,却顽强地挺立和抗争着。我害怕它会被吹倒。但暴雨过后,它依然挺立。它的树干更青更滑了,宽大的叶片更绿了。在它身上,几乎看不出被暴雨摧残的痕迹。我后来为此专门写了篇作文,成了全校同学的范文。再后来,三十年后,我曾在报纸上专门发表了一篇《青桐令》,我将我记忆中的最初的植物启蒙——青桐,刻进了我的文字里。
大概在我小学毕业时,有一年,村子里的人从青桐树上剥下树皮,沤在塘水里。渐渐地,树皮发黄,发软。他们捞起树皮,制作棕绳。青色的树皮制成了麻黄色的棕绳,结实,耐用。而到了四五月,黄豆成熟,村子里的人会将磨好的豆酱放在青桐宽大的叶片上,然后晒制。用青桐叶裹着的豆酱,香,且清洁。
多年以后,我回想起这棵青桐,并努力地回想着村庄上的其他植物。这时我才发现:它竟然是我们村庄上唯一的一棵青桐。青桐古老而充满诗意的历史,成了我最初的植物启蒙。而我更关注的是:这样一棵独立的乡村上的树,它让我知道了生命的界限与坚持。
狗几乎是农村孩子接触最早或者说最属于动物启蒙的家伙。它趴在地上,伸出舌头,不断地哈气。小时候,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为何需要哈气,后来才知道:它太热了,可怜的狗,一身皮毛,却只可以通过舌头来散发热量。它与睡在竹床上或者凉席上的人们往往隔着一段距离,有时候,也有人会丢一根烧红薯给它,它便欢快地吃了。吃完,还摇着尾巴,走到给它食物的人面前,看一会,才又回到它趴着的地方。这大概是感谢。狗在村庄里,是仅次于人的第二大存在。它们成群结队,白狗,黑狗,黄狗,花狗……各种狗,都是现在所说的纯种土狗。它们在村庄里游荡,见到人一点也不陌生,更不惧怕。它们闻到哪一家传出食物的香气,会蹲在这家人门前。直到人家送给它们食物,吃了,再叫上几声。然后,再去另一家。

狗在村庄上身份特殊。外面有人进了村庄,特别是夜晚,一只提前发现的狗开始叫唤,接着会有很多条狗叫唤。叫唤声让村民们警惕。这时候,这些狗就成了我们村的狗。因为它们担负起了警戒作用。但更多时候,它们属于更大的范围。狗群会不断移动,春天的时候,它们在村庄上嬉戏,可很快,它们便集体消失了。有人说它们去更远的庄子了,那里有吃的喝的,还有花枝招展的母狗。事实上,这说法是对的。以前,江淮丘陵地区,一到春天的四五月,便是粮荒。人都没了吃的,何况狗?但往北或者往更南,田地相对较多,粮食也相对充裕。狗的迁移,出于生存的本能。但它很快教会了村庄上的人:流动才是生存的第一法则。
狗与村庄上人的关系,在还是孩童时期的我的眼里,十分复杂。大人们对狗,既厌恶,又亲近。厌恶时,会拿着竹竿追打。亲近时,又给它们吃的,喝的,有时候,还带着它们去城里。一些女人,还会临时起意,拿着洋红给狗化妆。狗在村庄上生生不息,但有一件事还是终于被我发现了,那就是:那些年老了的狗,会在某一天,突然从村庄上消失了。它们去哪了呢?
其中有一条大黄狗。它个头高大,威猛。有好几年,它是村庄上狗群的头儿。孩子们喜欢跟在狗群之后,唆使它们互相追打。我们很快就看见:那只大黄狗,长期处于狗群的外围。它很少与哪一只狗亲近,也永远都不曾离开狗群。一旦有野狗进入村庄,它往往第一个冲出来。有吃的喝的时候,它往往站在后面,等那些小狗吃了,才吃。大热天,村子南头的几个孩子玩水,其中一个女孩子不知怎么地,就顺着陡坡滑到了深水区。孩子们吓得哭叫,狗群跑了过去,大黄狗站在塘边上叫唤,接着,它做出了让人吃惊的举动。它跳下塘,游向落水的孩子,然后咬着孩子的衣服,将她拖到了岸边。大人们赶来时,狗群已经散开了。大黄狗依然昂着头,走在狗群的后面。

那年冬天,一群外地的野狗经过村庄。它们在栀子河边集结,时不时地到村里来游荡。村子里的鸡丢了,晾晒在簸箕里的米粉肉丢了,女孩子们挂在竹竿上的花衣裳也丢了……村子里有人怀疑是进了小偷,但大黄狗它们瞧出了端倪。一场狗群之间的战争无可避免地爆发了。村子里的人听见在栀子河边,狗声沸腾。半天之后,大黄狗拖着残腿,带着狗群回到了村庄。野狗群远远地逃离了。栀子河边,留下了一地狗毛,与残耳断腿。村子安宁了,老人们给大黄狗多添了一碗饭。但年关快到时,它还是消失了。我曾问老人们:大黄去哪了?
真的,从此我再没有见过大黄狗。狗群由一只白色的大狗开始负责。若干年后,我终于弄懂了老人们说的“它去很远的地方了”的意思。大黄狗在生命即将结束时,选择了远离人群。它在孤寂之中,体面而有尊严地离开了。
狗给村庄上的人以最初的动物启蒙。村庄上的人,虽然与狗不远不近,但却时时感到一种观照。除了野狗群,村庄上还有大量的家养狗。这些狗与狗群完全不一样。它们往往都待在自家门前,主要的职责是看门、捉老鼠。狗一旦成了家养狗,狗的脾气、习性都渐渐磨掉了,有些甚至还会染上“坏毛病”。村中间大伯家的黑狗,看起来毛顺眼亮,一见着人就摇尾巴。但却暗地里偷吃小鸡。这可了不得。要知道,那个年代,小鸡是很重要的家庭财产。鸡能生蛋,蛋能换盐。鸡是日常生活中活钱的大多数来自。黑狗吃鸡吃得隐蔽,它不仅吃了自家的鸡,还吃了别人家的鸡。直到某一天,被主人当场抓住。大伯心善,毕竟养了好几年的狗,他舍不得杀。但又不能留着,便委托出门搞副业的人,将狗带到江南去丢弃。三个月后,一只瘦得皮包骨头的野狗进了村庄,直奔大伯家。大伯反复瞅着,最后认出了就是他们家的黑狗。他只好留下它。但这狗吃鸡吃上瘾了,恶习不改。大伯再次让人给带往江南。它又泅着江水,跑了两百里路回到了村庄。如是者三,它后来死在了长途奔波而带来的病痛上。它的尸体是在栀子河边被发现的,头朝着村庄。大伯在河边挖了个坑,一言不发地埋了它。
很多年后,洪庄成了开发区的一部分。田地没了,丘陵没了,栀子河也没了。我曾专门寻着旧迹,找到了那块我记忆中的土地。站在那里,秋风萧瑟,我不仅仅听见了人声,也听见了混杂在人声中的那些高高低低的狗叫声。
清晨五点,天光熹微。秋风中,村庄还一片静寂。但这片土地上,一场庄重而盛大的送别,已悄然展开。所有人都沉默着,除了主事的偶尔交代几句。声音在这一刻成了多余。屋子外面,风吹着老槐树,发出“沙沙”之声,但它们传播到屋内,却更增加了静寂的程度。父亲穿上暗红的袍子,格外冷峻。他头戴孝帽,手里拿着白瓷碗,缓慢地出门,往左,再转过老屋角,往东。一百米后,他到达剃头大塘,下了塘埂,用白瓷碗舀起半碗水,双手捧着,又沿原路回来。然后恭敬地放在寿材前。

祖母那年已经八十三岁,在乡下,在那个年代,她算得上高寿。她已生病半年,卧床不起。其时,我们家正在重新建造房子。孩子多,老房子不够住了。因此,半夜,我们被喊起来的时候,房子还是半拉子工程。祖母已经坐在大椅子上,喉咙里发出很大的咕噜声,就像灶间拉风箱一般。我缩在人群之后,有些害怕。祖母换了一身新衣,她久病的面容,苍白,但却平静。她咕噜了一阵,在父亲和其他人的哭声中,便没了声息。很快,祖母被移到了灵床上,也就是靠墙的一块门板上。
那一刻,祖母好像还在。但三天后,父亲从塘里取水回来,我突然觉得:祖母已经真正地不在了。生理意义的死亡,在村庄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离去。宣告离去的,是仪式,是合上的棺材,是进入的黄土,是所有人都离开坟山,重新再回到村庄上的日常生活。
那一次,我没有问。关于死亡的启蒙,总是以猝不可防的方式出现。我由此知道:村庄上,一代代人就这样离去。他们活着,是村庄的一分子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世世代代,不断绵延。而他们离去了,村庄还得一样地活着。村庄还得劳作,还得生息,还得绵延。每个离去的人,都是村庄这部大书中的一个字,他们永远在——生的时候,以直立的形式存在;死的时候,以消隐的形式存在。
村庄是朴素的,因此对于死亡的理解,也是朴素的。后来,我也看到过村庄上许许多多人的死亡。在村子中间那条狭长的巷道里,曾经住着一位我的婶婶。当然,等到我在村里满地跑时,她已经同我的伯父离婚了。原因是不育。她离婚后一直住在村子里,一个人,房间里黑漆漆的。厨房里的烟往往弥漫着,加上没有窗子,屋内即使白天,也很难看清。她娘家已经没了人。跟她往来的,也只有村子里一些善良的妇女。小时候,我们大家常常从巷道里过,都加快脚步。不知为什么,总感到害怕。有一天,孩子们发现:她的屋子的门被泥给糊住了。大家疑惑,稍大的孩子说:她死了。葬到山上去了。所谓的山上,就是丘陵地上的小土墩。若干年后,洪庄拆迁,我们家族迁坟,她——也在其中。一副窄小的木棺,一方小小的墓碑,标示着她曾经的生活以及与我们家族的关联。每年清明,我们会去祭奠她。每次,我总想记起她的点滴。但是,哪有呢?她就像一滴水,落在黄土里。同样是一生,却令人唏嘘。站在她的坟前,我总仿佛能看见她幽怨的眼神,在小巷道那木门前,遥遥地望着……
有死就有生。死是大事。生更是大事。只是大事的仪式感不同。死,庄重而幽寂。生,喜悦而开放。村子里每年总有几个孩子降生,每个孩子的降生,都伴随着红蛋,糖果,三朝喜酒,有的还得做七朝,一百天,周岁。长大后,我惊奇地发现:生与死,在对时间的对应上竟是如此鲜明。孩子降生,叫七朝,一百天,周岁;但人死了,叫做七,百日,周年。前者,本身就透着股新生力量的灵魂;而后者,就如同燃烧的表纸,飞作白蝴蝶时,亦透着无边的虚诞。村子里有孩子出生,女人们会聚在产妇屋内,男人们则在屋外的场子上聊天。特别是孩子的父亲,虽然同样在聊着天,抽着烟,但神情明显是焦急的,期待的。他的手甚至发抖。一旦听见屋内传来“哇”的孩子的哭声,他便急着往屋内跑。但跑到门口时,会停下来。他等着接生婆出来,然后告诉他:“生了个带把的”或者“喜得千金呢”。
在村庄上,腆着大肚子,是女人们之间最大的话题。孩子们会期待着大肚子里跳出小娃娃。但可爱的小婴儿,真的被抱到眼前时,往往会让孩子们吃惊:就这么个小不点,将来真的会长成像我们一样的人?事实上,确实就有些没有长大。有些大肚子的女人,连同她的孩子一道从村庄永远消失了……生与死就这样联系到了一起,它们之间的界限也因之被打破。生之欣悦,很快转成了死之悲哀。而也就在无数的死之悲哀中,才更能体现出村庄上的生之欣悦。

洪放,1968年生,安徽省作协副主席。文学创作一级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秘书长》《追风》《撕裂》等,散文集《南塘》《幽深之花》等。小说曾发表于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中国作家》等,并被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《新华文摘》等转载。曾获安徽省社科文艺出版奖、安徽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冰心散文奖等。


特别声明:以上内容(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)为自媒体平台“网易号”用户上传并发布,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。
天眼陨落!2.6亿巨资打造,全球最大望远镜成垃圾场?线
33岁陕西籍清华女硕士驻村干部因病去世,孩子不满1岁,曾遍访村组帮销农副产品,打造发展新思路
明年起避孕套要征税了!国家催生又一猛招,网友:早就没欲望了
小米高管集体被验证码轰炸——这是真的遇到了网络黑产,还是转移近期口碑下滑的注意力?
,星空体育官方app